在對費蘭特作品的改編中,《骯臟的愛情》與《我的天才女友》確屬佳作,《暗處的女兒》表現不俗,因而由Netflix推出的劇集《成年人的謊言生活》甫一發布就吸引了觀眾駐足。
失效的大IP
 【資料圖】
【資料圖】
然而六集成片正式上映之后卻撲得悄無聲息,“費蘭特”這一IP竟然失效了。首當其沖的原因是選角,飾演女主角喬瓦娜的演員面貌硬朗,看起來不像會為青春期煩惱所困,且表演過于克制,沒能演繹出成長的動搖與澎湃。肩負著使女主愛情幻滅這一職責的羅伯特,也不似小說中那般高大英俊,幻滅感大打折扣——羅伯特的飾演者還曾在HBO出品的《我的天才女友》中飾演成年恩佐,幾無變化的造型與表演使人頻頻跳戲。
此外,強烈的實驗感拍攝手法壘高了理解敘事的門檻;過多的配樂喧賓奪主,幾無停頓與留白;偏冷的色調氛圍與以集體、政治坐標來反思個體成長的主旨也并不恰切。
這或許是所有改編需要處理的問題:如何在向觀眾傳遞原著的同時兼顧二度創作者的個人表達。
劇集始于家長會后,母親與父親分享著女兒在學校中的不佳表現。母親將此歸咎于青春期的到來,父親則將原因指向了一個明確的名字——維多利亞。她是喬瓦娜的姑姑,是父親眼中不成器的妹妹。這番話傳到了在門外偷聽的喬瓦娜耳中——偷聽,青少年靠近成人世界時的謹慎姿態。借此,喬瓦娜接觸到上一輩的糾紛以及家族的隱秘往事,生活的邊界由此擴張,姑姑居住的下城區向上城區少女張開懷抱。
費蘭特的小說慣于借助對稱結構來完成人物的塑造和心靈的探尋,兩個角色親密而自帶分歧,并在生活場景的變動中展現出此消彼長的角力。例如《煩人的愛》中的母與女、《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萊農與莉拉,彼是此的隱喻,此是彼的鏡像。《成年人的謊言生活》亦如此,姑姑與我,互相審視,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隨即再分別完成各自的生活。
上城與下城,以空間表征著父親與姑姑的不同身份、階級、生存現狀,兩個空間通過喬瓦娜實現交匯。這樣的對比手法在李滄東的短篇小說《鹿川有許多糞》中也曾現身。小說從兄弟倆的重逢引出對比與對自我的再認識:哥哥俊植一路奮斗,從學校雜工成為了教師,并和妻子擁有了自己的小公寓,看起來生活似乎得到了改善。隨著同父異母的弟弟玟宇的來訪,平靜的生活泛起了漣漪。借助弟弟的眼睛,讀者不難發現哥哥的生活和其居住地一樣充滿了矛盾。鹿川,聽起來很詩意,符合中產生活具備的某種閑適優雅之印象。實際上,這個名字高雅的地方周圍盡是工業廢水與生活污水,以及不斷散發惡臭的糞便。
外來者的視野可以揭開生活的面紗,迫使其露出真實底色——玟宇揭開了俊植的,姑姑揭開了上城區的,喬瓦娜則揭開了成人世界的。
甜膩的省略號
費蘭特是聰明的作家,善于懷疑,并且往往能夠通過細小的懷疑來撕裂生活,使其煥發出骯臟的“光彩”。在《成年人的謊言生活》里,這個懷疑的起點是青春期少女偷聽父母對話之后產生的疑問——我究竟丑不丑?丑,是隱喻,這個隱喻指向福樓拜與包法利夫人——愛瑪看著女兒犯嘀咕:“真怪,這孩子怎么這么難看。”費蘭特認為這句嘀咕不僅精彩而且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她將這股破壞力移至喬瓦娜的成長中。在《成年人的謊言生活》小說面世之后,《洛杉磯書評》曾如此評論:“喬瓦娜學到的一點就是,不讓自己被‘丑陋’嚇退或煽動,與其進行虛偽的粉飾,不如選擇‘愉快’地直面那種丑陋。和她拋在身后的那些說謊成癖的成年人不同,喬瓦娜準備去面對無限廣闊世界的本來面目。”
小說作者更在意的是探索意義的過程,劇集在意的是賦予探索以結果與意義。一至六集,劇名分別為:美麗、相像、痛苦、孤獨、愛情、真相。六個詞匯放在一起,拉扯出一部青春言情劇綽綽有余,勾連一條人物成長伏線卻力有不逮。而劇集的野心并不止于刻畫青春,而是要在少女青春的故事基底上鋪展國家政治的年老衰敗。“征服紅色的春天,在未來太陽升起的地方”的歌聲多次回蕩在劇集中,彰顯著導演積極構建“少女——政治”夢幻聯動的昂揚之姿。
父親是虛偽的,身為左翼理論教授,吃著魚子醬喝著香檳討論社會不平等,卻對乞討之人大聲斥責加以驅趕。羅伯特也是虛偽的,張口閉口言及上帝宗教云云,但對此毫無領悟與感受。導演為了展現那不勒斯男性共同的軟弱,甚至特意給兩人安排了一場辯論,讓謊言遇到謊言。兩個男人實際上只是揮舞著不同理論武器的一類人,道可以是宗教精神也可以是左翼思想,只要能夠幫他們走出下城區,遠離底層生活就已足夠。
清晰誠實,言簡意賅,迫使讀者感受粗暴,這是費蘭特通過文字展現出的剛硬堅定。劇集卻因為含混曖昧式的表達而與之發生偏離。費蘭特曾為《衛報》寫過一年專欄,后結集為《偶然的創造》出版,其中一篇專門寫其對省略號的看法,“在我寫的文章里,我覺得省略號是一種賣弄風情,就像當人們半張著嘴,眨眼睛,做出一副驚訝的樣子。總之我覺得這些停頓太甜膩了,好像是為了取悅于人。”
《成年人的謊言生活》劇集臨近結尾處,一面破敗的意大利國旗在蔚藍的海面上搖擺,這是我們熟悉的套路——欲以個人成長之“小”見政治、階級、宗教之“大”,大小之辨背后隱含價值序列的高下之爭,省略號式的表達使劇集陷入含混無聊。在費蘭特筆下,歷史政治是背景,人才是被表達的主體;而在導演這里,人反而是展現歷史政治的工具。歷史的雄音不振,現實的回響飄散,散于咸濕海風中。
在給評論家戈弗雷多·福菲的信中,費蘭特寫道:“我特別討厭那種敘事:就是系統地講述今天的那不勒斯是什么樣子,現在的年輕人是什么樣子,女性變成了什么,家庭的危機,還有意大利存在什么樣的問題,諸如此類的書。”很遺憾,劇集《成年人的謊言生活》就是這樣的敘事,假借上城區少女的青春殘酷物語為殼,包裹著朝向政治批判的宏大格局。既無力強攻現實腐朽,又放任“人”從鏡頭中悄悄溜走。
邊緣的重要性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英譯者在紀錄片《費蘭特熱潮》中曾提到一個詞——smarginatura。它原是一個印刷的術語,意指紙張的邊緣,譯者將它翻譯為“界限消失”。這一翻譯越過“邊緣”,從而抵達了屬于邊緣之外的某種結局。2013年詹姆斯·伍德在《紐約客》討論埃萊娜·費蘭特的小說,以“women on the verge”為題,意為“邊緣的女性”。顯然,他們都注意到了費蘭特前期小說文本中“邊緣”之重要性。
“邊緣”所包含的其中一種指向是階級。出生于那不勒斯上城區知識分子家庭的先天條件,使得喬瓦娜不必像《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萊農一樣,直至暮年才能夠在回顧往事時感慨“我的整個生命,只是一場為了提升社會地位的低俗斗爭”。通過青春期的家庭與愛情危機,她早早看穿了有識之士的虛偽,知識并未雕刻他們的靈魂,只是塑造了他們的話語。左翼也好,宗教也罷,于父親、于羅伯特而言只是獲取階級躍遷機會的工具。所以她毅然出走,逃離巧言令色的低俗,逃離與謊言無異的種種主義。掙脫成人世界的謊言,掙脫那不勒斯,掙脫命運。
《成年人的謊言生活》的最后一集名為“真相”——歷經謊言之后必然抵達的結局。喬瓦娜與女伴搭上了前往未知的列車,她們下定決心要過一過自己的“失敗”人生——因為所謂的成功,也不過是如父親或如羅伯特。屬于女性的斗爭僅僅是成為她自己,不是要成為某位左翼教授的女兒,也不是成為某個神學才俊的女友。
這或許也是費蘭特筆下所有女性的斗爭——在成為自己的路途中,她們不斷克服著時間的流逝與那不勒斯的圍困,也不斷印證著:女人,是永遠的異鄉人。(趙晨)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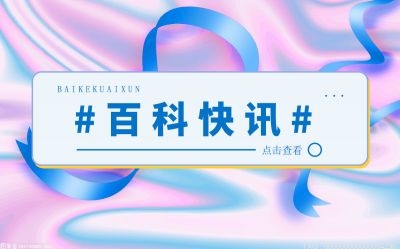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