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近期,根據德國作家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小說《西線無戰事》改編的同名電影上線。這已是《西線無戰事》第三次被改編為電影。此前,1930年、1979年拍攝的電影《西線無戰事》都是美國人的作品,這次改編權移交到德國人的手里。1928年德國《福斯報》在開始連載雷馬克的小說時,編輯評論道:《西線無戰事》是無名士兵的第一座真實的紀念碑。這部沒有傾向性的小說,卻是一座比石頭還要堅固、比礦石還要持久的紀念碑。這紀念碑激動人心,充實人的頭腦,給后幾代人展示了最恐怖的戰爭紀實圖像。
滿腔熱血的德國青年博伊默爾懷著英雄理想投身“一戰”,當他被派往西線參戰,目睹的卻是殘酷的饑餓、血腥和死亡……新版影片更注重感官沖擊,近視距、微型化地將戰爭景觀投射到個體的身體。博伊默爾深嵌戰爭四年時間,戰爭帶來的身心虛脫,戰爭間歇的放縱,讓年輕士兵身體僵硬、心靈迷失,只剩下驚恐不安,蜷縮在塹壕里,等待著末日審判。影片開端沒有參戰恐懼安撫的矯情,一頓炮火就把戰爭硬生生地塞入每個新兵的神經,死亡也撲面而來;遠山、叢林、霧靄都是鬼蜮的組合,表情麻木的士兵奔跑在戰場上,如同飄蕩死亡原野上的鬼魂。影片畫面色彩濃烈,灰色、白色、黑色是底色,慘白的臉孔、黑黢黢的焦土、暗紅的血,是慣常的景象。泥淖是電影反復出現的畫面,泥坑里搏斗、泥淖里匍匐、泥淖上跋涉,所有軍士都陷入戰爭的泥淖,思想情感都深深地被埋住,連拔出來的力量都沒有,泥淖的寒冷、潮濕和粘性把軍士身上的感覺都剝蝕掉了。他們所有的權利就是虛妄的等待,等待虛妄,不想掙扎和反抗。相反,每個軍士習慣了死亡,只有死亡能修復他們的脆弱,了結戰爭難以傾訴的痛。正如膝蓋受傷的賈登,速求一死,用調羹戳破動脈自殺。地獄的戰爭場景,妖魔化的軍士,碾壓一切的機器怪物,具體而微的垂死畫面,呼哧呼哧的死亡氣息,全面展示了個體戰爭體驗,寫實了底層軍士的戰場蠕動。影片畫面凝重徐緩,靜水流深中讓戰爭兜售者看清戰爭的產物,在靈魂深處清算自己的罪責。
再精彩的故事在重復講述中也會失去生動和新鮮。新版《西線無戰事》卻沒有因為反復拍攝而產生審美疲勞,恰恰因為它沒有制造美、制造故事,只是在展示戰爭體驗和痛楚。“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戰爭有時會被狂熱分子鼓吹或夸耀。《西線無戰事》是反英雄反戰的,它用塹壕的真實訴說戰爭對人的摧殘和剝削。“為了皇帝、上帝和祖國”,一群青年學生被蠱惑,帶著英雄的夢想走向戰爭的泥濘。一場炮火下來,青春被槍炮熱度烤焦而枯萎,信仰熱度抵不住死亡的寒冷。尸體、殘肢塞滿了戰壕,只有姓名牌證明了曾經有一個人來過戰壕,參加這場戰爭。戰爭摧垮人,靠的不僅是坦克一樣的鋼鐵猛獸,還有時間。西線戰斗的四年,每次戰斗只能前進數百米,因此戰況報告里只寫著“西線無戰事”,但黑色政治謊言之下是西線戰場300多萬年輕人橫尸殞命。
影片以平民化的視角書寫主人公博伊默爾的故事,他沒有來得及成長為戰士,就失去了戰斗理想,失去了熱愛與仇恨的能力,失去了思考力,只剩下虛妄,本能地“活命”成為他存在的最高準則。為了活命,他要開槍、搏斗、殺戮;失去思考力,意味著他徹底被戰爭的恐怖填塞和毀滅,淪為戰爭的活僵尸。與凱特一起偷盜農戶的食物,是他在戰爭之余能找到的最大快樂,即便這靈光一現的生活松弛,也很快被死亡定律絞殺。影片描繪的死亡困境是種痛感警示,面對痛苦死亡人才有確切的現實感,才能自覺抵制罪惡戰爭對底層人的壓榨。
新版影片中沒有1930年版“抓蝴蝶”和1979年版“臨摹云雀”那樣的藝術曲筆,徹底割斷了戰爭與藝術的詩意聯系。面對戰爭的殘酷,藝術無力將其轉化為超然的審美想象,只有無力地哀鳴與斥責。批評戰爭決策者在談判桌上的延宕,批評無能的將軍為了所謂的屈辱,驅動軍士們在停戰前發動最后一輪攻擊,徹底送掉了主人公的性命。博伊默爾的死是必然的,但也是猝不及防的,他小心翼翼地掙扎卻倒在停戰的門檻上,那死亡瞬間的直立令觀眾不由地驚恐戰爭抽離生命的無情,激起對戰爭的恐懼抽搐。
新版《西線無戰事》沒有縱深地挖掘故事,而是將焦點放在了那些在大歷史中后知后覺的小人物身上,讓觀眾看到時代鏡像深處的淚水,感受被戰爭遺棄的普通人的不幸,反戰的共識更具說服力。歷史經驗應在反復閱讀中沉淀,痛感經驗應不斷傳遞繼承,拒絕遺忘和平的主張才可能有堅實的理性基石。西線無戰事,愿天下再無戰事。(作者雷軍系原軍事經濟學院基礎部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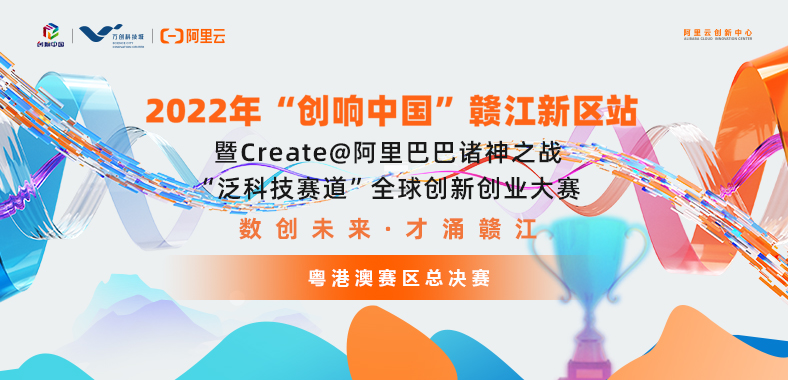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