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一句話、一個“理兒”,為了一個能相信自己的人,她不辭勞苦地倔強著、苦澀著、堅持著,但人生的死結并不因個人的委屈和辛苦而舒展。如同鬼打墻,李雪蓮二十年的路程竟是在一個圈子里兜轉循環;又仿佛拳頭打棉花,她不息的勇氣意志總得不到對等的回應。鼓樓西戲劇出品的荒誕現實主義話劇《我不是潘金蓮》,在劉震云原著的厚實基礎上,經卓別靈改編,由丁一滕導演,展現出獨特的舞臺魅力和復雜的生活滋味。
前些年,《我不是潘金蓮》這部長篇小說已經通過銀幕獲得傳播。作為馮小剛與劉震云強強合作成果,又有眾明星的號召力,同名電影產生過相當影響。想來大多走進劇場的觀眾都熟悉這個故事:農村婦女李雪蓮為多生一個孩子與丈夫秦玉河假離婚,不想弄假成真還被污名為“潘金蓮”,為還原真相和為自己正名,她走上了艱難的告狀之路。在基本故事相同的前提下,什么樣的舞臺形式才能不辜負小說?不輸給電影?才能展現戲劇藝術的創造?
 【資料圖】
【資料圖】
巨眼下的死胡同
一進劇場,就看見舞臺被半透明的球形幕布包裹,仿佛懸著的一只觀看眾生的巨眼。仔細看,巨眼上的紋絡是略微變形的樹木枝蔓的投影。舞臺上的故事,盡可以被當作是巨眼看到的人間糾葛。而這糾葛,是一個又一個死胡同里的沖撞。
戲開場后,伴隨一聲聲漸強的心跳,幕布內燈光亮起,主人公李雪蓮站在斜坡式轉臺正后方,紅色上衣將她突出出來。轉臺緩慢轉動,轉臺上的人以努力保持平衡的姿態慢動作行走,并隨著幕布升起,一一走下轉臺高處挖出的臺口。舞臺上只剩下李雪蓮一家三口,三人姿態活躍起來。爸爸追打兒子、媽媽護擋,讓第一場戲充滿游戲感。一對恩愛夫妻、一點生活諧趣、一個蓋房子的人生理想和一個意外懷孕后假離婚的謀略,形成滿臺鋪展的力量和期待。然而,這段溫暖生活的交代僅幾分鐘,情節便急轉直下——秦玉河背叛了李雪蓮,人生的逆轉把李雪蓮逼進了死胡同。筆法之干脆,入題之果斷,讓開場的熱情有多濃烈,轉折后的現實就有多冰冷。而這種對沖、起落、反轉,其實是整部戲一以貫之的情感結構和劇場節奏。
接下來,我們看到,在李雪蓮艱苦的告狀之旅中,山窮水盡時偶有柳暗花明,但柳暗花明后又總是新的窮途末路,如此收放張弛,循環往復,一出戲就演完了。你盼望她能贏嗎?那些草率處理她的官員上面雖然還有“青天”能為她做主,但她要證明經過法律程序的離婚是假,又怎么可能?除非秦玉河講良心,承認當初的約定。然而,秦玉河若是有良心,還會失約且落井下石咬定她是潘金蓮嗎?一件事變成另一件事,一個人的無情牽出一串人的無情,李雪蓮滿心殺意但手無寸鐵,蒙冤受辱卻無法證明。因為告狀這事兒從起頭就是條死胡同。但是,執拗的她不相信。不相信居然沒有人相信她,不相信這世界真假不辨、對錯難勘。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可能比竇娥還要冤。竇娥死后尚有飛雪、血濺白練、亢旱三年證明她的冤屈,李雪蓮卻完全無計可施。現實中,沒有神跡。雖然她寧可把自己和秦玉河假離婚約定的人間最后見證者——一頭牛臨死前的搖頭當成神跡,決定畫上告狀之旅的休止符,卻耐不住被不相信她的人們再次激怒。而當她從大頭那里重新體驗到人生的美好,再次決計不告狀時,卻發現自己被設計了。被欺騙的憤怒讓她重整旗鼓,人生卻給了她新的嘲弄和絕望——秦玉河死了。李雪蓮即便想告狀,也無人可告了。巨眼下,她只是不斷從一個死胡同走進另一個死胡同罷了。
黑色幽默調性
沒有人會否認,這是一個悲劇。一個啞巴吃黃連的女人拼卻二十年好光陰,就算有無盡的勇氣和意志,到頭來依舊一無所獲。然而,你替她哭時會被逗笑,你為她笑時又會悲從中來。因為劉震云對人生這種“擰巴”的苦澀認識,是以黑色幽默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丁一滕則在舞臺上以同樣的幽默回應了劉震云的智慧。
除了把原著中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段落轉化為夸張的舞臺動作,譬如李雪蓮找屠夫老胡幫忙殺人時抖出如秦香蓮訴狀般的一長串名單,丁一滕還保留了劉震云式彎彎繞的風趣表達。李雪蓮與王公道那繞了八竿子遠的親戚關系、對人解釋不清的自己從牛那里獲得的不再告狀的提示等,都讓交流成為語言游戲與陷阱。而幽默的肢體動作、川劇變臉、說唱藝術、河南方言貫口、男扮女裝反串等,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讓劇場里笑聲不斷。
舞臺呈現的可貴處在于,導演用了那么多喜劇手段,卻謔而不虐。因為其目的不是搞笑,而是解嘲。說不出來就唱,走不下去就爬,愛不成就恨,哭不得就笑,所有的笑點都在恰當的敘事節奏上。每到情感緊處,這一笑就松了松。
驚艷的舞臺
在《我不是潘金蓮》中,群眾演員的調度、象征性舞臺語匯的使用,以及戲曲元素的加入,都對劇作的“荒誕現實主義”起到了加持作用,展現出了戲劇藝術以簡代繁、以虛托實的舞臺魅力。
庭長、專委、院長在轉臺上兜圈子的走位,縣長、市長出場時隨從們亦步亦趨,首長會議發言時“趙乾”“孫禮”等眾下屬正襟危坐,正干活的化肥廠工人們換個陣形即變身為唾棄李雪蓮的眾人,這些按劇情需要變化角色身份的群眾演員,還原了大多數人無名但成陣的人間狀態。而那個內外三圈的轉臺,通過布光變化,有時散發出生鐵精鋼的金屬色澤,帶著工業時代的清冷絕情,有時則被投以白底青花邊沿圖案,成為一個瓷盤,讓李雪蓮成為盤中餐。在舞臺光色變化中,紅光用的最多,且總是大面積鋪瀉。借助它,角色的內在沖動如熱血奔涌。當李雪蓮被污名為潘金蓮時,舞臺上方垂吊下一個巨大的、白色的、沒有五官的旦角的“空臉”造型,這是一個面目模糊的潘金蓮,可以被安上任意一張女性的面孔。隨后,又有一張只有鼻子的圓臉造型垂吊在“空臉”后面,輕輕搖蕩,那鼻子像極了無臂女人的上半身,也像一條沒有袖子的超短連衣裙。而后,一襲紅衣的京劇旦角潘金蓮款款登場,開始了與李雪蓮的隔空對話。原來,潘金蓮也有一肚子委屈。這是戲曲角色潘金蓮第一次出場。接近尾聲時,再次出場的她干脆說自己也曾是李雪蓮。這是丁一滕對劉震云原著主題的增容。
全場戲中,女主角張歆藝幾乎沒有離開過舞臺。劇終,精疲力竭的李雪蓮蜷身躺在舞臺上被圍觀,球形幕布緩緩降下。開場場景復現:眾人又在尋找平衡中行走,心跳聲一聲強似一聲,良久不息。至此,《我不是潘金蓮》完成了圓形敘事,亦即死胡同里的內循環。
劉震云說過,《我不是潘金蓮》是一個螞蟻變大象的故事。而螞蟻變大象及相應的多米諾效應,是劉震云作品一以貫之的話題,是來自無解人生的一聲嘆息。舞臺劇《我不是潘金蓮》突出了劉震云那一聲嘆息,并內化了《一句頂一萬句》中的孤獨感受、《一日三秋》中的笑話心態,以簡潔又豐富的舞臺形式、緊鑼密鼓又充滿停頓的舞臺節奏,完成了一場從開始就注定沒有出口的循環。而這種循環就是“荒誕現實主義”中的“荒誕”和“現實”。(谷海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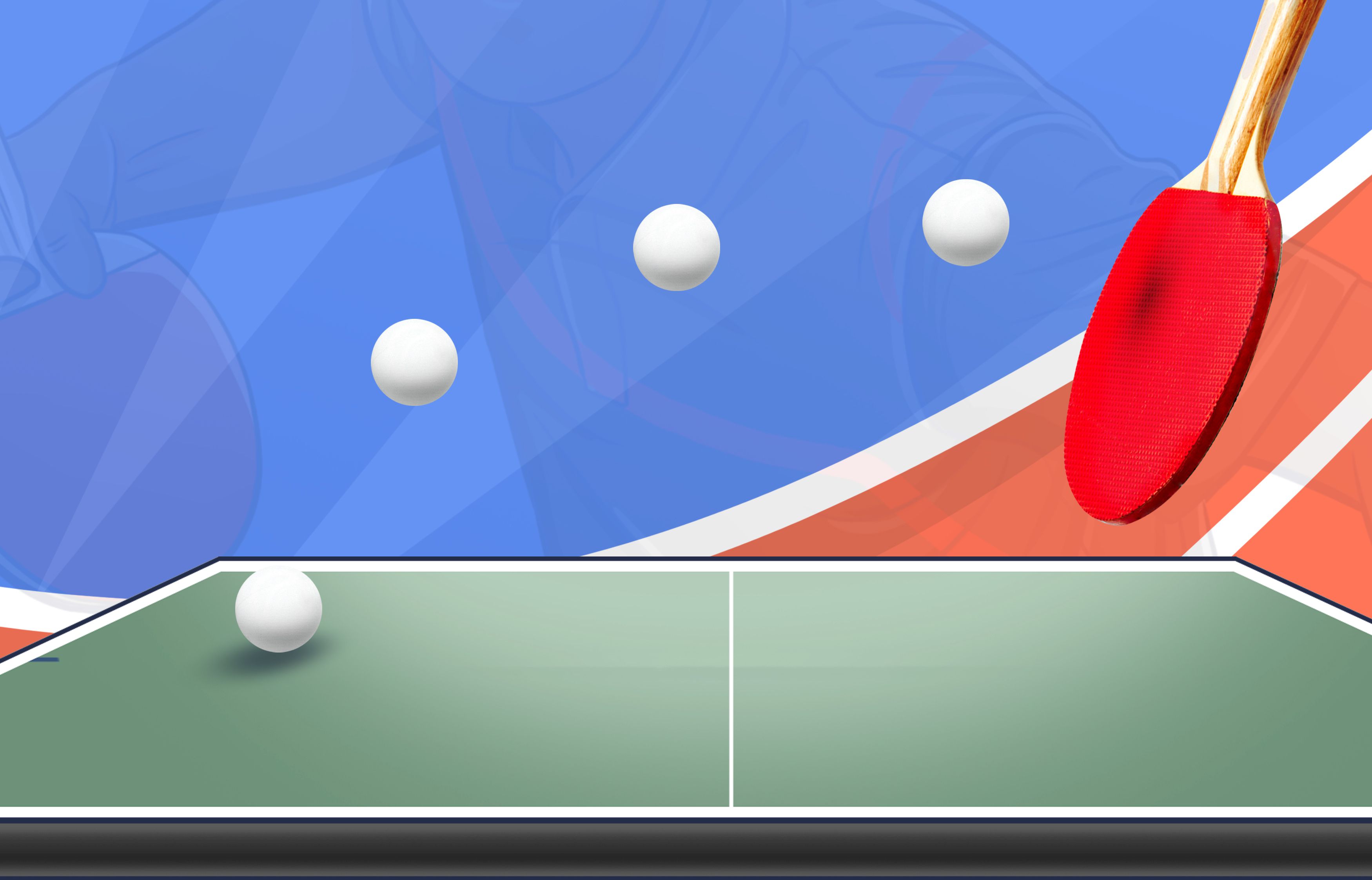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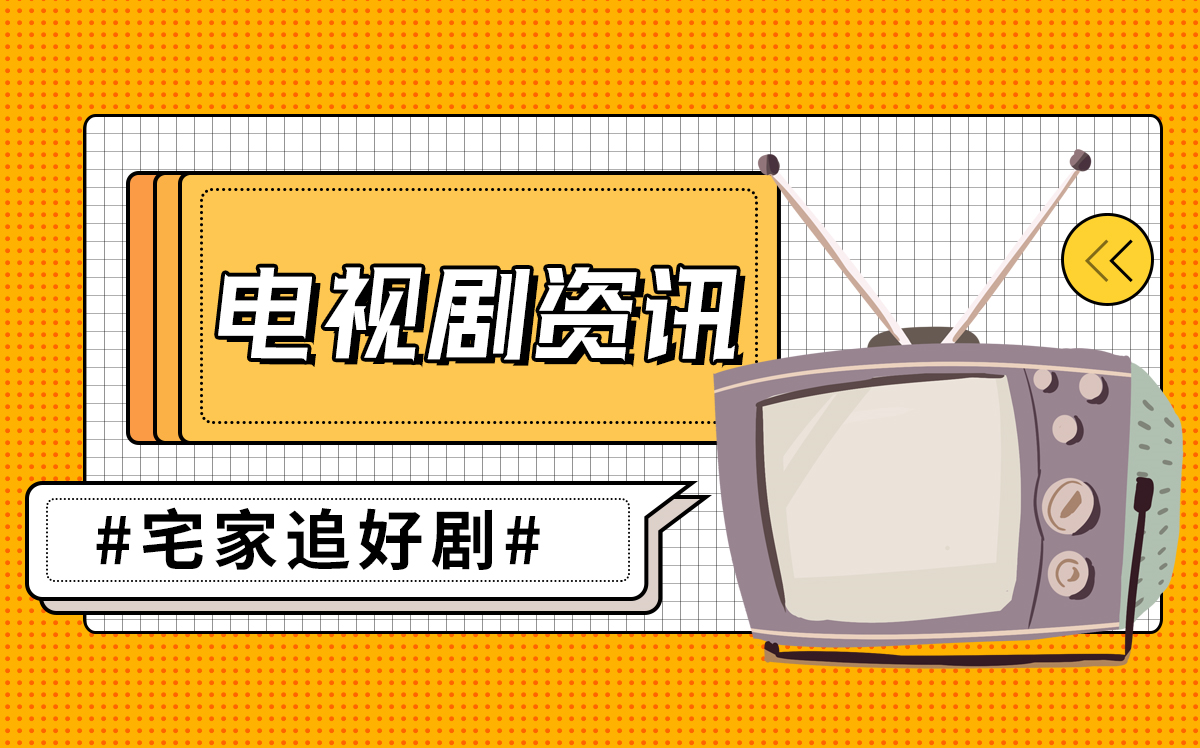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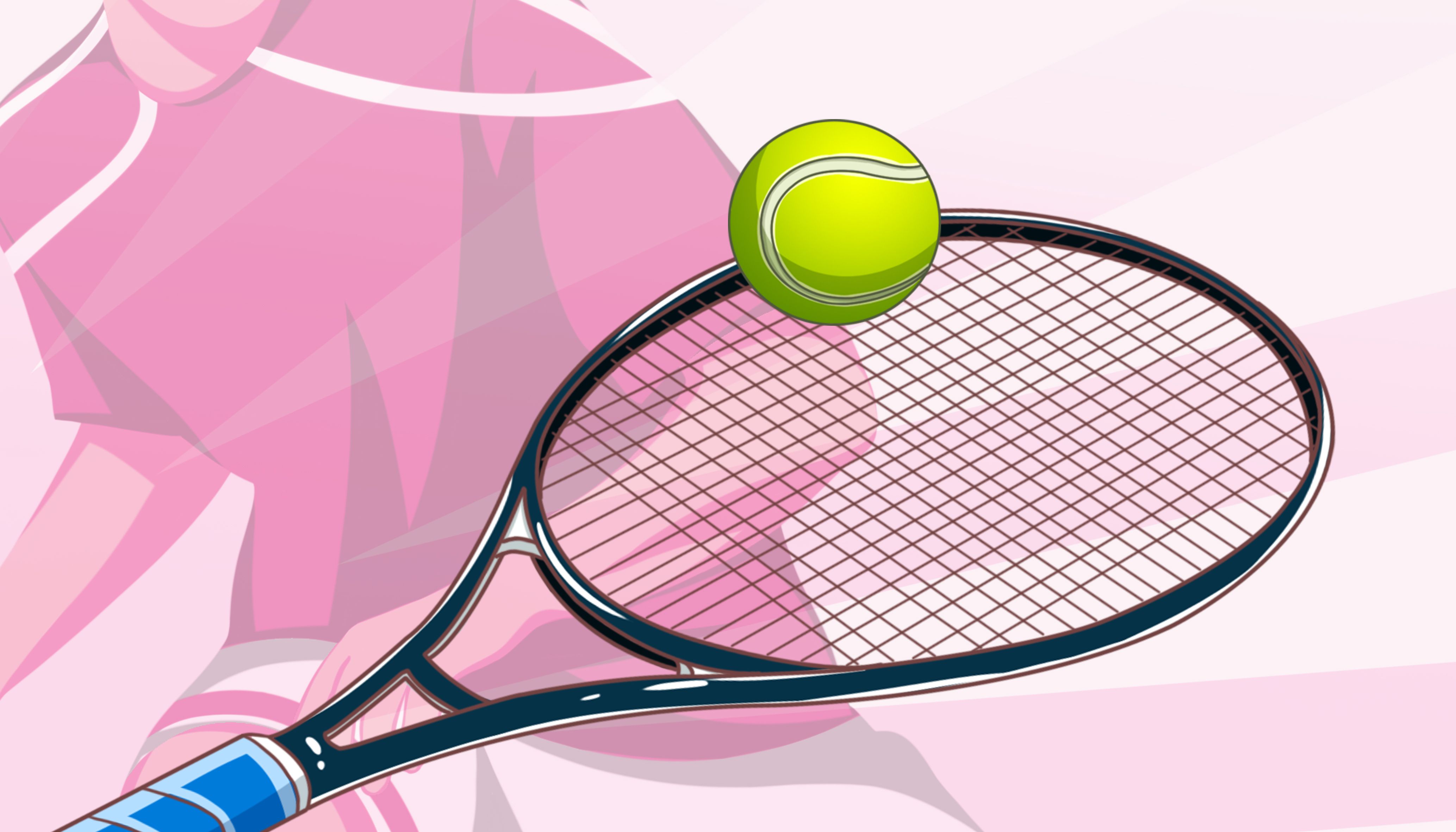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