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三年,《樂隊的夏天第3季》在立秋后歸來。“夏天”已經遲到,樂隊會不會讓人失望,可能是樂迷們既期待又擔憂的問題。
“你上《樂夏》,你上它有啥用啊?”是二手玫瑰在表演時向樂隊們拋出的問題,也同樣適用于樂迷和節目組,并且在不同的時代常問常新。在這個時代搖滾被續寫了怎樣的內核?對樂隊的意義是什么?《樂夏》對樂迷的意義又是什么?“這一季《樂夏》,我們就主打一個享受音樂。”馬東在節目伊始明確了第三季的主旨,或許剛好給出了回答,但卻也不僅如此。
 (相關資料圖)
(相關資料圖)
多元生態,構筑民族化聲景
“這是搖滾嗎?”“夠搖滾嗎?”是《樂隊的夏天》過往兩季節目中,每每提出就會引發爭論的問題。似乎除音樂本身的編曲、演奏之外,樂隊的風格是否符合參賽資格常被作為決定競演成績的一大因素。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樂隊的夏天3》共集結27支樂隊,涵蓋數字搖滾、英式搖滾、朋克、后朋、電子、迷幻、民謠、爵士、世界音樂等多種風格,形成多元生態。節目在前期樂隊招募的環節,并未框定樂隊的類型范疇;在表演結束后的談話環節,不再將界定樂隊風格作為“必答題”。通過打破刻板單一的類型化桎梏,彰顯開放包容,以樂隊原生氣質為主進行扶植的價值取向。
小眾與大眾兼顧,傳統與當代關照,民族與世界接軌。來自五湖四海的樂隊將具有民族特色的聲音元素融入到音樂創作與表演中,在聲音——媒介——受眾的多層關系中,通過聯覺產生跨越時空的畫面,想象出本不在場的地理意象,通過表征空間構筑民族化聲景。
來自內蒙古大草原的安達組合彈奏馬頭琴、口弦琴、陶布秀爾等傳統樂器,模仿樹木、動物等自然的聲音,把豁達的心態、與草原、天地之間的對話用音樂表達出來,實現了傳統音樂的時代詮釋,形成了世界共通的意義空間。廣西樂隊瓦依那使用鋤頭、樹葉等原生態“樂器”還原農作的聲音,體現了扎根土地的生命力。二手玫瑰融合東北二人轉、民樂、搖滾樂,輔以東北民俗中紅配綠的視覺標簽,以荒誕夸張的表演、反諷的歌詞表達態度。來自東北、內蒙、廣西、廣東、云南、四川等不同地域的聲音與意義空間的關聯,呈現出源自中國大地,緊扣時代脈搏的藝術生態。
平等共情,提供重啟的力量
受眾通過競賽規則、鏡頭時長等洞悉節目的底層邏輯,從而判斷權力的分配是否合理,這是輸贏之外受眾所關注的重點。競演類節目中,權力主要體現為投票權和話語權,投票權決定排名,話語權影響輿論走向。權力歸屬所反應的價值取向是決定節目口碑的關鍵因素。
《樂夏3》對樂迷稱謂和投票規則做出了調整,將掌握較多話語權,常因犀利點評被質疑“說教”的“專業樂迷”改名為“樂隊友友”,避免“大眾”與“專業”對比,有精英話語之嫌。取消票數梯度,將大眾樂迷(1票)、專業樂迷(2票)、超級樂迷(10票),改為人均1票。去除等級之分,只有角色之別,關照節目“平等享受音樂”的主旨,從底層邏輯到頂層設計都更為簡潔、統一,使節目立意更加純粹。
從不同站位的評判到沉浸其中的共情,在理性與感性互滲的天平中,《樂夏3》更傾向于提供情緒價值。
樂迷與樂手就樂隊經歷、創作背景和歌詞含義展開交流,從而將個體經驗和創作意圖置于時代參考系中理解、互文,產生共鳴。通過同一首歌或者同一支樂隊,在不同的命題中找到了相同的答案,獲得重啟的力量,這便是音樂的魅力和齊唱的意義。正如大張偉所說,“音樂最大的魅力是在于,它讓臺下無論是八萬人、三千人,都變成一個人,那時候就是被音樂賜予的時刻。”
播出到第三季,《樂隊的夏天》已經擁有了較強勢的市場和文化代表性,無論是對老牌樂隊還是新生代樂隊都有很強的扶持力度,但從節目制作角度仍存在可精進之處。期待《樂夏3》能將知識科普延續,以提升受眾的音樂素養,獲得穩定的受眾增量。畢竟,《樂夏》的意義不只是挖掘樂隊、制造沸騰,更多的是向樂迷提供不可替代的安定感,因此情緒安撫與知識科普的結合也將成為差異化競爭的優勢。對于《樂夏》,似乎已不用再執著于追問“搖滾精神是什么?”,從節目形態來看,多元、不設限的樂隊陣容,平等、赤誠的心靈撫慰,固執、熱烈的自省革新,不停尋找答案,永遠保有個性,已經回答出了這個時代關于搖滾、關于樂隊的部分真意。(高貴武、吳雨桐)
高貴武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視聽傳播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雨桐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
關鍵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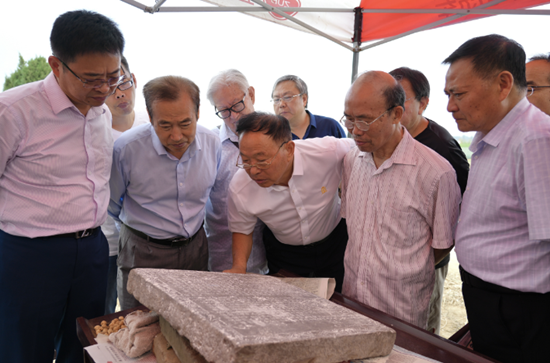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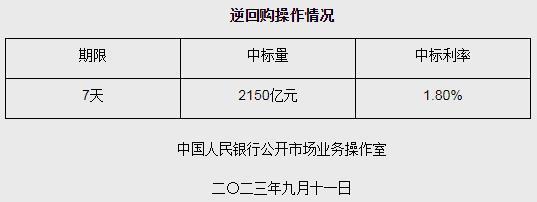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